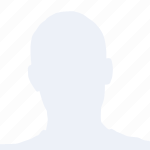日 志
后现代技术地理
后现代技术地理
摘要:在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后现代视阈中,对技术的反思不能仅仅局限于时间的维度,空间地理学的分析更为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贫穷问题的关注是技术空间分布不均的结果;在空间政治经济学领域,主体际问题成为后现代技术的中心逻辑;在对权力与统治的警惕中,后现代技术建构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
关键词:后现代;技术;地理学;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后现代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从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主要是立足于当下,分析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从时间的维度来说,所有的后现代都是“现代的后现代”[1]。技术变迁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工业生产方式,“因此,后现代化与改变了的工业景观有关:产品轻便灵活;职业结构剧烈变革,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工业占多数;一个被压缩的世界,其中新技术不仅造就新工艺,而且还带来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2]在后现代图谱中,技术不仅具有传统的时间性变迁的谱系,相对于现代性而言,后现代更看重技术的空间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不仅要考察技术在时间中的凝聚,更要重视技术在空间地理上的分布与展开。
一、贫穷的技术与技术的贫穷
从总体上来说,贫穷是指一种物质上的匮乏。贫穷的技术就是指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资料的生产活动所需要的技术。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而言,后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资料比较丰富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消灭了贫穷的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论是从国家与民族之间,还是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相对的贫穷、甚至是绝对的贫穷依然存在。从政治哲学层面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正义或公正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归之于分配或再分配的问题。而从技术地理学来看,这却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运动的结果:贫穷地区或者贫穷的人群在技术上也同样是贫穷的。
缺乏解决贫穷的技术,造成了贫穷人群的出现;贫穷的人群在技术的产生、使用和传播方面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尽管这并不是后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但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就是后现代技术地理的基本逻辑。如果说前现代技术是一种相对公平而言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和传承,现代技术是一种科学知识线性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后现代技术则具有不同于前二者的特点:一方面,后现代技术更强调大资本的投入和集团化的人力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后现代技术还具有系统化、标准化的特点,在后现代社会,“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标准”。因此,后现代社会技术空间分布的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
正是由于后现代技术地理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后现代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穷人的经济状况,因而作为“经济学良心”的“穷人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穷人经济学产生的标识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理论回应:一是经济学开始更多地关注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被修正为同时具有非理性特征的社会人,经济活动不再是个人事务而成为共同体的活动,自私的人性与利他的伦理道德的冲突成为经济主体间的首要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是道德素质而成为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二是从“凯恩斯革命”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转向,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弱势群体和贫富分化问题,市场不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跑马场,政治力量、法律体系和制度设计都开始介入其中,从崇拜作为客体的市场的力量转而依靠主体的政府力量再到多元主体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相应地从前现代、现代阶段转向了后现代时期。[3]
二、空间政治经济学:技术的逻辑
从技术的社会作用来看,后现代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技术产生、传播和更新速度的加快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全球化趋势造就的“地球村”带来的“时空压缩”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哈维认为空间与时间的概念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不同的社会制造了性质有所不同的空间与时间概念。“首先,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定义,跟任何个人和制度皆须回应的客观事实的全体力量一起运作。”“其次,客观空间和时间的定义,深深地纠结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 [4]每个社会都建构起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社会一旦发生了变化或成长,相应的其空间与时间概念就必须改变,以容纳社会再生产的新的物质实践。这种改变既可以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部强加的。“藉有征服、帝国主义扩张或新殖民支配,列强便安置了新的空间与时间概念。”[5]与此相应,20世纪晚期随着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组织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时空压缩感,是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哲学等人文科学的视阈中,技术的本质并不是技术,不是人类生存的工具、手段,而更多地就是人类生存方式本身。人类通过技术展示自身的存在,客体世界通过技术向人类“打开”(open),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是人类命定的存在。因此,客体、主体与主体际就成为解读技术逻辑的关键词,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技术拥有自身的逻辑。
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研究对象和活动对象主要是面对相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类而言的客体——自然界。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为了能够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就必须与自然开战,以征服自然为最终目的。技术作为人类征服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尽管这时也有一些先哲开始思考主体性问题,但由于人的理性之光还比较微弱,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揭开作为客体的自然之迷,因此,人类总体上还处在神话和宗教的统治之下。
在现代社会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开始成为技术交往的中心。这一时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在康德看来,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6]的状态。开启了人类理性之光的启蒙运动也成为以“大写的理性”和“大写的主体”为特征的现代性的开端:一方面,理性对宗教的“去魅”和科学的迅速发展成为技术进化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和大量非自然的人造物的出现也强化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和对理性的信心。然而,现代性的后果却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元叙事话语占有了解放的霸权,技术的“返魅”又造就了新的神话。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或控制形式,操纵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一个集权主义者。[7]
而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则是技术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转换:从生存问题、发展问题转换为主体际问题。这个时代的学者们运用文化批判、微观政治学、消费社会学、大众传媒批判等方法,通过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知识系统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谱系学考察,揭露和批判了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认为在这个语言符号取代暴力、再生产性社会秩序取代生产性社会秩序、多元与差异取代统一性与元叙事的后工业社会,如何跨越主体际之间的差异鸿沟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复主体性、互主体性、类主体性等等解答方式。[8]其实正是技术自身的逻辑造就了技术社会的悖论:人的主体性与技术对社会的统治同时加强,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解决主体际这一“美杜莎之谜”。
三、无定向变迁:技术乌托邦
在生存论视阈中,技术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自然赋予人类的动物本能就可以维持肉体的生存和类的繁衍。因此,“就像动物王国的其他种类一样,人类完全可能不用火与工具就能维持生存。”“技术是一种多余的产物。”[9]技术造就了与自然界对立的人造物世界,产生了与自然进化有所区别的技术进化路线。技术进化模式的解读源自于人类多样性的需求,其关键词是创新与选择,包括心理、知识、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10]而所有的技术进化的背后都是对理想生存方式的盼望与期待,这就是技术的乌托邦。
“从昔日的乌托邦的角度上看——昔日的乌托邦宣传一种极乐世界(die Ein-Heils-Imagination一种幸福的想象)——后现代当然意味着告别乌托邦。”[11]在后现代看来,乌托邦本身就是对权力统治的肯定与向往。现代性是在反对宗教神话的同时所创造的新的神话,“启蒙的神话”或“理性的神话”,因此,后现代是反乌托邦的。后现代对乌托邦的批判或反对主要表现在用追求民主与平等的多元论来代替会导致极权的统治的一元论。“但是,后现代告别乌托邦并不意味着它不再代表乌托邦,而意味着它代表与传统的乌托邦截然不同的乌托邦,即一种修正和超过传统的乌托邦的乌托邦:多样性的乌托邦。”[12]
现代性技术的特征之一是货币化或可计量性条件下的同质化趋势:在金钱面前的平等消除了先天的等级制社会。“社会地位的价值的货币化也可以导致个人(即占据地位者)价值的货币化,以及普遍人类关系的货币化。”[13]现代技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以合乎理性为标准,以符合社会消费需求为目的,是一个可以科学预言的控制系统。而后现代技术更侧重于主体之间的交往、沟通与联系,加入了更多的非理性元素,其变化的速度、方式、方向都难以估计,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无法捉摸。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性的工业社会向后现代知识社会转向的过程中,知识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对知识的“元话语”或“元叙事”的怀疑成为进入后现代的标志。[14]社会的功能性分化造成了主体的异化和社会角色的破碎化,信息的增殖与裂变带动了主体间的紧张感并造成了信任度的下降。技术的社会反过来又成就了社会的技术:技术不仅仅成为统治社会的力量,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巨大的网络。
The Technical Geography of the Post-modernity
Heng Xiaoqing WeiXingmei
(Institu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Jiangs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view of the post-modernity, the thought about technology cannot only be analyzed about the time. The analyst of the geography is more important. From the economics the attention about poor is the result of uneven distributing of the technology space. In the view of the space plutonomy,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subjective becomes the core logic of the post-modernity technology. On guard about the power and the governor, the post-modernity technology constructs the utopia of the anti-utopia.
Key words: Post-modernity; Technology;Geography;
[1] 参阅[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 [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3] 参阅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66页。
[4][美]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5] [美]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6] [德]康德:《历时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7] 参见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8]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9] [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0] 参阅[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0页。
[12]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0页。
[13] [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4页。
[14] 参阅[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