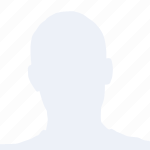日 志
“知天命”的烦恼“知天命”的烦恼 房汉廷 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他乡明月,日日追随。看看染霜的发际,确知老已至之。昨日跨入“知天命”大限,心下杂陈。去日多多,来日少少,却还有无尽的烦恼丝。 第一个烦恼是我相信什么与不相信什么。自幼主动接受与被动灌输了很多有关信仰的东西,也不断被动地击碎、重构、再击碎、再重构,结果行囊中只有大量破碎的瓷片,没有一件真正的瓷器。这个烦恼,近期有所缓解,在笔者的《杂谈汉民族信仰》中有了阶段性答案。 第二个烦恼是我吃什么与不吃什么。少年时家贫,食物匮乏,从没有想过哪些常规食物能不能吃以及怎样吃的问题,及至中年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当我第一次看到1605剧毒农药喷洒在三天后上市的蔬菜时,当我看到一只鸡雏可以在一个月内长到 第三个烦恼是我说什么与不说什么。上天予人以嘴,确定了两大基本功能:吃饭和说话。在吃已经极其危险的情势下,说就更危险了。幼时遭遇“文革”,每日都看到那些因“说”获罪的人,心下庆幸自己当时尚不能言;年轻时赶上改革开放,放谈成为一时之鲜,笔者也是嘴快心直,结果差点被“封嘴”;如今已到中年,对说什么更是噤若寒蝉。如我这般的“口力劳动者”,不言则无饭吃,言的没有听众无趣,言的听众太多死的更快。这种纠结已经多年,曾经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这般告戒我:做人不能讲假话,那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做人也不能讲真话,那样会对不起别人;做人只有讲套话,不伤人也不害己。如法炮制数次,确实有效,可也确实无聊,多么希望我也是天生的哑者啊。 第四个烦恼是我写什么与不写什么。嘴上惹祸还可以抵赖,笔上出事那是板上钉钉的咸鱼了。中国古代尚有言官制度,即使是君王也是有所忌惮的,可如今……有位颇有名望的学者曾经说过:制度重于技术。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没有好的制度就没有好的游戏规则,技术越先进导致的灾难可能越大。可是,制度建设是可以研究的领域吗?是可以秉笔“求是”的吗?笔者以前曾经认为能的,如今越发困惑了。难怪有人说“三代以降”,中国思想穷矣;“始皇以后”,中国政治荒矣。 第五个烦恼是我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人立天地间,很多人幼时都曾经想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及至成年才蓦然发现很多都属于痴人说梦。笔者力主躬行,然行之维艰,且闹的上下不安,指责漫天。友人观之,不忍让我如此愚顽下去,只引我乘坐玉渊潭到昆明湖的游船上一游。游毕,友人问我有何感悟。其实,我没有任何感悟,只好据实而讲——买了张票,坐上船,吃吃喝喝,说说笑笑间就到了昆明湖。友人大悦:这就对了,你只需要一张船票钱,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你不是就快乐地到达目的地了吗?是啊,已经上船的人,还费什么力气呀。
|